贾维斯·考克,英国流行音乐中被诅咒的诗人:“过去是一个谎言我们都有一本完全虚假的官方自传”

贾维斯·考克有一个诀窍。这位来自英国谢菲尔德(Sheffield)的音乐家在不太罕见的情况下不得不担任电视或电台的采访者,他会准备“不超过10个问题,涉及4到5个不同的话题”,然后让谈话顺利进行。如果他被困住了,或者怯场了——就像他采访他的偶像之一莱昂纳德·科恩那天差点发生的那样——他就会求助于他准备好的一个问题,即使这个问题不重要。
然而,当他被面试的时候,这个技巧就不起作用了。和Cocker在一起,谈话似乎总是流畅的……但它是通过意想不到的渠道进行的。他被问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开启了一连串的思考、轶事和回忆,他躲在角质框眼镜后面,带着幽默、节俭和关心滔滔不绝地说出来。
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酒店接受EL PAíS的采访时,Cocker承认:“我意识到自己往往会漫无目的。”他在城里宣传他的回忆录《好流行音乐,坏流行音乐》“你问我具体而直接的问题,我给你详尽的答案。但如果说我从写这本书中学到了什么的话,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,事情比看起来要复杂得多,因此,没有简单的答案,”他耸耸肩。
《好爸爸,坏爸爸》是他几个月来挖掘记忆的结果。从字面上看:在这位音乐家住在伦敦的房子里的一个小阁楼里,他存放了“几乎数量惊人的物品,从口香糖包到肥皂块、笔记本、俱乐部传单、音乐会门票、明信片、吉他挑片、照片、衬衫、玩具……”
Cocker开始写“多年来堆积的一堆疯狂的垃圾”,因为他确信,在某种意义上,它包含了他自己故事的本质。还有他的乐队Pulp的故事。“这是我童年时的一个计划,它让我成为我唯一真正想成为的人:一名流行歌星。我从13岁就开始想要这个了。我甚至还没学会弹吉他呢!”
![“During the year I spent in New York alone, [I was] dedicated full-time to being a star. It was awful,” says Jarvis Cocker.](http://www.lofnews.com/file/upload/202401/23/163038181.jpg)
不久之后,他对青春期幻想的投射变成了一个有点不稳定的音乐项目,为此他寻求“同伙”。
“我的榜样一直是披头士。对我来说,追求独奏家的职业生涯似乎是一个无聊得多的选择。”对Cocker来说,即使是在乐队没有唱片、没有音乐会、几乎没有排练的那些年,以及乐队的领导者在谢菲尔德(Sheffield)慵懒地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,或者在伦敦(London)“毫无信念”地学习艺术的时候,纸浆乐队依然存在。
从1978年到1993年,这群人在沙漠中经历了一次很长的旅行。然而,在1994年,他们终于以一张非常及时的专辑《他的和她的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一年后,紧随其后的是风靡全球的《不同阶层》。从一天到另一天,Cocker从一个地下艺术家变成了音乐前线的表演者。世人发现了一位令人敬畏的叙事歌曲作家,他既有雷·戴维斯(Ray Davies)的英式风度,又有罗宾·希区柯克(Robyn Hitchcock)的幽默和日常魔力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长得瘦长、留着不太可能的发型的近视男孩在舞台上也变成了一头野兽——史无前例地集戏剧性、精致、真实和魅力于一身。如果说达蒙·阿尔巴恩和加拉格尔兄弟是“英国流行音乐”革命的名义领袖,那么科克就是这场革命被诅咒的诗人和影子领袖。
这一成功是他人生中“最令人不安”的几年的前奏,在这段时间里,他实现了儿时统治世界的梦想,并最终成为一个改变了的人,他解释说,“不一定是一个更好的人。”我希望(我没有变成)一个彻头彻尾的白痴……但我确实是一个多疑、痛苦、虚荣的家伙。”他承认,名声和成功对他非常不利。“当我在14岁的时候想象,一旦我成为一个流行歌星,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,我认为我不会住在房子里,而是住在豪华酒店里,有管家,没有床单要换,也没有衣服要洗。我会整天躺在床上看《蝙蝠侠》。”
这个梦想在《不同的班级》的成功之后实现了。“在我独自在纽约度过的那一年里,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成为一名明星的工作中。太可怕了。”
这些天,在写《好流行音乐,坏流行音乐》的续集时,Cocker想知道他将如何描述坠入地狱的经历。这本已经出版的书涵盖了更早的时期:“从我在谢菲尔德的一个普通家庭的童年,到我在搬到伦敦之前住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的那些年。”

这本书应该是别的东西。“这是一篇关于我的创作过程的冗长而无聊的论文。起初,我想叫它《书是一首歌》。”他把它想象成一部“有引言、第一节、桥段、副歌和第二节”的作品。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“缓慢而不稳定”地完成这项工作。“那是因为我是一只乌龟。我几乎总是完成我开始做的事情……但是按照我自己的节奏,不着急。”
Mónica他的文学经纪人卡莫纳(Carmona)在一次书展上为他争取到了一份“宏伟的合同”。“她只提供了几段话就足够了,我解释了我的想法,这很模糊。她从集市回来后对我说:“贾维斯,你的书已经卖出去了。现在,你要把它写出来。’所以我开始工作,因为她相信我,我不想让她失望。”
2018年,在他完成与加拿大音乐家奇尔·冈萨雷斯合作的专辑《Room 29》的宣传后,考克就专注于创作本应被称为《This Book is a Song》的歌曲。但是,尽管如此,他还是无法开始。“工作了几个月后,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位编辑,她以一种让我大吃一惊的残酷的诚实告诉我,我写的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只有一个非常简短的部分是可用的:我决定清空阁楼,开始讲述我保存在里面的一些物品的故事的那天的编年史。编辑告诉我,她觉得这很有趣:“忘掉最初的想法吧,从你的储藏室里出来的垃圾才是真正值得的。”’我听了她的话。”
在捡起这些物品,给它们拍照,思考它们对他的意义,以及为什么他决定把它们保存这么长时间的过程中,科克尔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。“过去是一个谎言。我们都有一个完全虚假的官方自传,我们告诉自己和任何愿意听的人……但这只不过是一个谎言。这是我们想成为的人的生活,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。当我们面对赤裸裸的事实时——在一本相册里,一个旧记事本里,或者一个堆满垃圾的储藏室里——真相就会浮现出来。有时,这是令人不安和痛苦的。”
贾维斯·考克(Jarvis Cocker)的真实故事,是从他心爱的物品的角度讲述的,也许是“一个对过去有着迷信和非理性依恋的人,他从童年开始就保留着肥皂条,因为设计的变化和原始包装的记忆丢失让他感到沮丧。”考克接受了挑战,展现了自己的本来面貌:一个“梦想成就伟大的人,把自己最好的时光都用来浪费时间的人……一个一直有雄心壮志的人,但他的意志力和毅力常常让他失败。”
回顾过去也让他意识到音乐在他的生活中是多么的根深蒂固。“如果你问我最古老的音乐记忆是什么,我的肩膀和脖子又会有一种奇怪的发痒感,就像我和妈妈一起听收音机时一样。我喜欢戈登·莱特富特的《如果你能读懂我的心》之类的歌。我当时太年轻了,对听到的任何事都信以为真。我真的相信无线电精灵能读懂我的心思,进入我的大脑。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。”更多的迹象表明,年轻的考克与命运有不可避免的约会?他出生于“1963年9月19日,那天《她爱你》登上了英国音乐排行榜的冠军”。他的父亲“在1970年离开了家,那一年披头士乐队解散了。”对他来说,那一年意味着“纯真的终结”。

他那难以捉摸的父亲曾经在一个乐队里吹长号,乐队里还有乔·考克。“除了姓外,我们没有任何家庭关系。”一个Cocker最终取得了胜利,而另一个很快离开了音乐界。“我知道,我父亲听了那个命运坎坷的老故事,心里很难受。如果他呆在家里,也许他可以指导我弹吉他,我学会了独自弹吉他,缺乏天生的技巧,直到今天仍然伴随着我。幸运的是,不久之后,朋克音乐教会了我,几个和弦就足够了,这种技巧一点也不重要。(这是一种解脱),因为在13岁的时候,我因为不能演奏披头士的歌曲而感到羞愧。”他的祖父“只在圣诞节和一些生日的时候”演奏管风琴,他的叔祖父“在英国和德国的旅游小镇有一支乐队”,他也不能演奏。他的叔叔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,给他留下了“一条在德国风靡一时的带吊带的皮裤,但在谢菲尔德你不能穿,除非你准备好被羞辱。”
Cocker将他对音乐的热情归因于他的近视。“我一直很近视,有多重屈光度。奇怪的是,他们直到我五岁才发现(这种情况)。在我戴上第一副眼镜之前,我的清晰视力范围缩小到只有几英尺。其余的都是一堆模糊的东西……我不认识的面孔,被我绊倒的桌子和家具,直到足球砸到我的脸上我才看到它们朝我飞来。充满敌意的宇宙。但另一方面,声音的世界是一个清晰而友好的世界,我从未在其中绊倒过。”眼镜恢复了平衡,但在他的生活中,听觉世界比视觉世界更重要。
在《好流行,坏流行》的最后一段,Cocker讲述了一件最终改变了他生活的“创伤性”事件。“我不想(在这次采访中讨论),因为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折,我不想剧透。但我想谈谈我从中学到的东西。(这件事)教会我相信自己讲故事的直觉。通过观察我周围发生的事情,并将其转化为我歌曲歌词的叙事材料,我自己也感到惊讶。我发现现实是故事的非凡来源,甚至不需要对它们进行改造和修饰——大脑已经为你选择了重要的细节,那些吸引了你的注意力,也将吸引那些倾听你的人的注意力的细节。”
这一发现产生了几首名字普通而准确的歌曲,如《普通人》、《婴儿》和《你还记得第一次吗?》他的回忆录《好流行,坏流行》也是从这个现实中诞生的,这本书本想成为一首歌,最后却变成了帮助他恢复记忆的迷人咒语。
相关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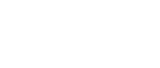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