加文·克里尔谈如何在百老汇生存、性、名声和制作自己的音乐剧

2019年,当演员加文·克里尔(Gavin Creel)第一次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时,他不得不“面对这样一个事实:我觉得自己不属于那里——这与我当时的生活感觉有点相似。”由此揭开了一个紧张的故事,讲述了一个演员在职业和个人生活中漂泊不定,试图在他生活的各个领域开辟新的道路。
这可能会让那些认识克里尔的人感到惊讶,他是2017年获得托尼奖的英俊百老汇明星,主演了《你好,多莉!》他在其中扮演科尼利厄斯·哈克他还获得了其他托尼奖提名(2002年,他在百老汇的处女作《彻底现代米莉》,2009年,他获得了《头发》),其他奖项(2014年,他在伦敦凭借《摩门经》获得提名,2023年,他在《走进森林》中的滑稽表演获得提名),并获得了许多好评。
但在他的新自传体音乐剧《继续前行:一个博物馆新手的自白》(MCC剧院,1月7日上映)中出现的克里尔是一个受损、质疑、温柔、机智、异想天开、好色、悲伤的灵魂。他说,至少他知道,他在大流行期间成为了一个抑郁、孤僻的人,这是他与“许多其他人”共同的经历。
在克里尔创作的《勇往直前》(与他一起演出的还有精彩的萨莎·艾伦、玛德琳·本森、克里斯·彼得斯、科里·罗尔斯、瑞安·瓦斯奎兹和斯科特·沃瑟曼)中,这位演员将对艺术的新热情结合在一起,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大厅里漫步,拷问自己的生活和艺术,他对性的喜悦,一段失败的关系,以及对自我的重新发现和恢复。
像许多在疫情期间被迫坐冷板凳的戏剧演员一样,他不知道戏剧是否会卷土重来;与大都会博物馆的合作——也就是这次展览——是他的全部。“在最初的几个月里,我们不知道人们是否还会想坐在剧院里——我们不知道。我想我必须卖掉我拥有的一切,放弃我所努力的一切,因为戏剧似乎将不复存在。我想,‘也许现在是时候搬到别的地方去做点别的事情了。’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这个项目。”
然而,他说,当时他对钢琴和工作有一种“爱恨交加”的关系——有时他觉得自己需要做点什么,有时却什么也做不了,这种自我施加的压力。最终能够在真正的剧院里表演他的劳动成果是一种“祝福”。

琼马库斯
47岁的克里尔知道,说自己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听起来有多老套,但“经历过并感受过中年危机,而且现在还在经历中年危机,我发现这是非常真实的。”你的前半生都在朝着你希望和梦想的方向前进,如果你找到了它,或者在它上面着陆了,你有时会想,‘这不是它。“你应该到达了,但是没有到达。我在寻找一些东西来填补这个悲伤和孤独的空洞。在人际关系中,这对另一方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压力,他们会说,‘我不知道自己是谁,不要让我为你填满那个空白。’”
克里尔觉得自己“被诅咒了,也被祝福了”,他希望这段艰难的时期是一个“间歇”,标志着他在这之前是什么样的人,以及他希望在这之后成为什么样的人,“我希望在我后半生的剩余时间里,他能成长起来。”
托尼奖颁给多莉!没见过高峰吗?“有一点,但不是真的。自从我开始做这件事以来,我一直对自己的工作又爱又恨——尤其是演戏。我真正想成为的是一名流行歌星。”他回忆起在《摩门经》全国巡回演出时在后台小便的情景,心想“这是我的人生吗?”他对这份工作心存感激,对他得到的所有好评心存感激,并试图通过放松来抵消自己的不安。
“每个人都认为我的生活很美好,但我内心觉得很糟糕——尽管看起来我拥有了我想要的一切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“我非常幸运,”克里尔说。《摩门经》之后是《她爱我》,然后是《你好,多莉!》“我不懂这部剧,但我不会拒绝一份工作。我最终找到了一个办法。(导演)杰瑞·扎克斯指导我。斯科特·鲁丁引导我。贝蒂·米勒给我带路。大卫·海德·皮尔斯拥有至高无上的优雅、美丽和优雅。每个人都很棒。我接受了,但当我接受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过着别人的生活。我在想,‘我该如何融入这一切?'
“每个人都认为我的生活很美好,但我内心觉得很糟糕——尽管看起来我拥有了我想要的一切。我真的为托尼奖感到骄傲,但我在大学毕业后的《成名:音乐剧》中也同样努力工作。在《她爱我》前一季,我同样努力地工作。而一个几乎完全相同的部分却没有得到任何关注。有一个赛季我一个奖都没拿,下一个赛季我什么奖都拿了。我只是不明白,但我意识到奖项不是它的意义所在。健康和人际关系方面发生的私人事情让我感到失落和破碎。”

朱丽叶塞万提斯
在《勇往直前》中,克里尔试图评估自己在一段让他心碎的长期关系破裂中的罪责——就像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那样。与此同时,他的声音“越来越老,我作为歌手的身份与我的声音捆绑在一起。如果我听起来很傲慢,请原谅。但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副好嗓子。我一直担心,‘如果我的声音出了什么问题,没有了它,我是谁?“疫情期间,我失声了。我感到非常悲伤。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抓住了我的喉咙。当我唱歌的时候,它听起来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
克里尔意识到他的身体整体上在发生变化,这提醒他,“作为一个同性恋者,变老是另一个完全不可见和无关紧要的层面。”我必须面对这一点。我一直在抓东西,试图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我的价值和价值,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外包给了一个衡量价值的行业,在这个行业里,我的价值取决于我是否赢得了一个奖项,或者我是否有一个主角,或者如果他们说得不对,我就会被他们摧毁。”
克里尔说,他一生都在与孤独作斗争,但他一直有他的狗沃利,“我的救星”——在他和狗狗分手六周后,它去世了。他也在大流行开始时感染了COVID,虽然他从未觉得自己会死,但这进一步损害了他的声音,以及他“失去了赋予你身份的一切”的感觉。
“这就像是,‘你不应该感觉糟糕,因为还有其他人比你感觉更糟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他说,克里尔的抑郁症非常严重,他都认不出自己了。“我应该是一个快乐的人,娱乐人们,让人们快乐,人们喜欢和我在一起。但在那个时候,我不会为了世界上所有的钱而想要在我身边。我不知道如何成为人们期望的那种快乐、外向的人。我觉得我的前任是唯一能让我感觉更好的人——但我们都认为这种关系是不对的。”
他说,当他如此沮丧的时候,他永远不会伤害自己,也不知道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抑郁定义为抑郁。而是在为自己的感觉而惩罚自己,在悲伤和孤独的感觉上加上责备和评判。“这就像是,‘你不应该感觉糟糕,因为还有其他人比你感觉糟糕得多。’”
最终,克里尔在《勇往直前》中找到了解决办法。他的导演问他是否准备好面对他所有的个人恶魔,克里尔很担心人们对结果的反应——他们是否会认为这是自我放纵,其中的我,我,我的数量是不值得的,“他们的问题更糟糕。”但我必须相信这是我的故事,我想分享它,我试图把它制作成一部鼓舞人心的戏剧,”他说。“我打算通过这个节目来治愈,希望能在世界各地巡演,帮助其他人。”
当被问及他现在怎么样时,克里尔说他很好。“孤独和抑郁不会消失。你不能把这些事情做完。”在节目中,他歌唱着孤独:“哦,我看到你回来了。我想你永远不会离开,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。”在克里尔的日常生活中,也存在着同样慎重的接受。写作和治疗一直是他最大的“治愈和应对机制”。他不敢主持这个节目,唯恐人们和评论家不喜欢它。但他知道他无法控制别人的反应。他只是想有机会“一次又一次”地表演它。他的一位主要投资者告诉他,“你不再是在创作音乐剧,你是在创作一种服务行为。”这就是克里尔想要用他的艺术做的,也是他希望人们从各种艺术中得到的。
克里尔的右手腕上有个纹身,上面写着"两者都有"这句话概括了他对生活中一切事物的态度,这些事物可能是美好的,也可能是可怕的,可能是欢欣鼓舞的,也可能是忧郁的。“我在一个万物的空间里。在47岁的时候,我意识到爱自己就是接受自己,而不是评判自己。如果我冒险和一个或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分享我的生活。如果我加入一个社区,同时爱上60个人呢?事实上,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集中注意力。我想说的是,我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放态度——我不知道和不理解的东西还有很多。”
难怪这首歌颂性的歌曲是这场演出中最出色的歌曲之一——他的角色是如何被大都会博物馆里所有肌肉发达的雕像所激发的。克里尔说,当时他正在听电子舞曲,萌生了这个想法。“我意识到每个人都在看着这些雕像,却不承认它们让他们感到多么饥渴。我不得不面对我想操所有这些雕像的事实。这首歌是关于性的羞耻,以及重新找回被人,胸部和鸡鸡吸引的感觉。不再有荡妇耻辱,尤其是因为荡妇耻辱归结为同性恋恐惧症和厌女症。这只是另一种方式,让异性恋白人男性的目光继续渗透到艺术世界。人们说有很多酷儿创作的艺术作品,但还是有很多作品出自同样的白人、异性恋艺术家之手。”

Eduardo Munoz Alvarez/路透社
这部剧的另一个主要主题是宗教,以及宗教对克里尔生活的影响,最终导致了他与上帝的对抗,最终同意或接受了上帝。
“我自豪地感受到上帝的祝福,”克里尔说。“我不相信我生命中的所有好运都是巧合。我相信我是有福的。我不再惧怕上帝了。我觉得我好像在和他合作。”他(在俄亥俄州的芬德利)被教导以正确的方式行事,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准备。他说,在他母亲那边,他的祖父母是门诺派教徒,他父亲是圣公会教徒。他在卫理公会教徒家庭长大,他的父母对当地教会的忠诚鼓舞人心。“这是关于社区和服务。他们安静而勤奋地服从上帝的教导。我们总是在吃饭前祈祷。
“我父母会把我扔在主日学校,那时
我读到的故事让我想,‘哦,天哪,我完蛋了。我不能是同性恋……——加文·克里尔
“我没有学习圣经或任何严格的东西,但我们从小就被教导我们是在与上帝对话。我的父母会把我丢在主日学校,在那里我会读一些故事,让我想,‘哦,我的上帝,我完蛋了。我不能是同性恋,即使我想看看那些男孩,上帝是一个站在讲坛上的人,告诉我同性恋是一种罪恶,那些人会下地狱。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,但那是我生存的基础。现在,我认为我生命中的快乐、美丽和机会都来自于诚实和真实。”
克里尔和他的两个姐妹被培养成“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家庭”,被期望进入优等生名单,否则我们就不能使用汽车,并成为优秀的模范公民。直到今天,我的父母都是最慷慨和服务至上的人。他们总是为别人做事。对我来说,这也意味着很大的压力,因为我知道我内心有这种东西,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尴尬、羞耻和伤害。当我25岁向父母出柜时,我很害怕。他们太棒了。我妈妈哭了一下。她说,‘不要参加任何游行。七八年后,我的父母在华盛顿游行,争取与我平等。”
他的第一位心理医生告诉克里尔,他出柜是在“夺回你的权力”,他的父母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与他无关;即使他们对他大吼大叫,把他赶出家门,他也会找到自己的路。“但他们没有这么做。当我对父亲说,我认为事情会比实际情况更糟时,他说:“我环顾了一下教堂,心想如果没有你,我的生活会变得多么无聊,这里有多少人问我们你过得怎么样。”当剧中提到的关系破裂,克里尔崩溃时,他的父母来照顾他,做饭,打扫,帮他哭出来。
克里尔长大后想成为一名流行歌星,模仿他的偶像惠特尼·休斯顿。他拥有的第一盘磁带是黛比·吉布森的专辑。他买了惠特尼所有的专辑,记住了她所有的歌:“我声音里的任何灵魂都是我试图成为她。”克里尔上六年级的时候,他的一个异性恋朋友给他买了一张惠特尼海报,后来当其他同学来找他时,他就把这张海报撕下来,以免他们认为他是同性恋。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他喜欢的是她声音的激情、丰富和独特。还有她的快乐。她的视频既性感又平易近人。她对每个人都有吸引力。”后来,他被惠特尼如何面对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人,以及她与罗宾·克劳福德的奇怪关系所感动。
有了两个姐姐,他“想尽一切办法吸引别人的注意”,但即便如此,他还是感到分裂——就像他后来长大成人后的感受一样——在“看着我,看着我”和“别看我”之间摇摆不定。他说,今天,他仍然不知道如何“建立许多人认为成名所必需的那种人格”。我喜欢在舞台上自由和真实。有人说我过度分享,或者我的身体像稻草人一样四处走动。我想我永远也成不了流行歌星,因为我对包装自己没有兴趣。你看出来了,我得了口拉肚子!”
粗纱架笑了。“欢迎成为中西部人。当你在俄亥俄州长大时,我们不会谈论性,我们不会谈论政治、宗教或你的感受。在《勇往直前》中,我公开了所有这些事情。现在我觉得憋在肚子里是有毒的。我喜欢中西部的生活方式,但人们需要彼此交谈或交流。”
“我知道这个行业不可能代表一切。我无法从它身上获得快乐,因为它没有心跳。它最终不关心a
次我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在密歇根大学学习音乐剧后,他在匹兹堡CLO剧团演出。在巡回演出《成名:音乐剧》和其他地区演出后,他于2000年代初登陆纽约,凭借《彻底摩登米莉》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托尼奖提名,这是他第一次在百老汇演出。
克里尔说:“我喜欢百老汇的Kool-Aid,喜欢这里的社区和它的性感,和朋友一起出去,和朋友一起喝玛格丽塔酒喝醉。”“我喜欢见到一些我崇拜的偶像。然后,老实说,花从玫瑰上掉了一点。新人进来取代你。生意的循环意味着我不能再爱它了。我知道这个行业不可能代表一切。我无法从它身上获得快乐,因为它没有心跳。它根本不在乎我。
“我看着公司在方便的时候利用我和其他人,然后经历了一段时间我找不到试镜机会。我不能从一个最终植根于资本主义的行业中获得快乐,而资本主义的根源最终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。”

沃尔特·麦克布莱德/盖蒂图片社
克里尔把这归功于哈丽特·塔布曼效应研究所的创意总监妮可·约翰逊的“了不起的工作”,他说:“这个国家的音乐剧是在吟唱和黑脸中建立起来的——这是我们不谈论的,但我们需要谈论它来治愈。”人们问为什么百老汇正在消亡。它建在一个充满毒药的墓地上。我目睹了种族主义的发生,却一直保持沉默,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声音站出来说话。我现在唯一能说的是,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再也不这样做了,感谢上帝让我们得到了清算。”
克里尔谴责了他最近听到的一些评论——“这个人得到这份工作只是因为他是黑人。”这是无稽之谈,种族歧视。说这种话的人是在说百老汇的每个白人都很好,我在这里告诉你,这不是真的。很多在百老汇有工作的白人不应该有工作。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敢肯定,有些人会认为,‘加文·克里尔太无聊了,太无趣了,但他一直在工作。他不应该。比他优秀的人太多了。“剧院里的白人没有讲述足够多样化的故事,他们没有为有色人种挺身而出。我们是问题的一部分。种族主义造就了音乐剧,至今仍无处不在。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对抗它。”
“我觉得自己既被奇怪地看待,又被性化了。这是一种复杂的感觉。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,我感到自由,但我也受到了伤害,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克里尔“一直都经历过性骚扰和不当行为,以至于我把它看作是我们在剧院里的行为。”不适当的摸索、评论、裸体、关系和不适当的身体接触一直存在。这对我来说也很难,因为我有时担心,当我们纠正明显错误的行为时,我们也有可能抹去一种文化,这种文化允许大量的同性恋者最终感到他们在一个可以欢迎、接受和交流自己性取向的地方。
“我觉得自己既被奇怪地看待,又被性化了。这是一种复杂的感觉。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,我感到自由,但我也受到了伤害,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文化,我延续了很多这样的行为。现在,重要的是在任何合适的空间和渠道上就所有这些事情进行沟通。”
正如他在节目中明确表示的那样,克里尔相信谈论性和庆祝性,而那些谴责酷儿谈论性的人,克里尔说,也是那些否认我们平等的人,他们目前正在参与一场诋毁变性人的联合运动。
谈到名声,克里尔说,他曾经希望人们知道他是谁,“并拥有权力和影响力。然后我意识到那是蛇在吃自己的尾巴。不管你有多大,你都想要更多。”当然,他喜欢社交媒体带来的粉丝,也喜欢教一个20人的教室,“他们看着我,好像我屁股里有阳光一样。”但是,克里尔说,他不能教这个班的学生成名,而是教他们如何表演,如何建立一个健康、长久的职业生涯。克里尔说:“我认为我可以比现在更出名,但我不想做这份工作。”“那时我才知道,我不想为了出名而出名。”
但在他凭借《你好,多莉》中的角色获得托尼奖之后,一切都急转直下了——提议、接近、普遍的嗡嗡声?

朱丽叶塞万提斯
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”克里尔说。“我告诉你,电话没有响。我赢得了托尼奖,我想,‘对我来说,有些事情将会改变。除了一件非常受欢迎的事——我现在是托尼奖得主加文·克里尔(Gavin Creel),我喜欢这个头衔。这意味着我再也不用拿托尼奖了。当我第一次获得托尼奖提名时,我也有同样的想法,我知道我将永远是托尼奖提名者加文·克里尔。’这是社会对我最大的褒奖,我非常感激。”
但除此之外,这并不是赢得托尼奖后发生的事情,而是“没有发生的事情”,克里尔说。“是因为我40岁不性感吗?”(这显然很荒谬,因为克里尔很有魅力。)同年,本·普拉特(Ben Platt)以《亲爱的埃文·汉森》(Dear Evan Hansen)获奖,从本质上讲,一切都发生在他身上,也许是因为他还年轻,事业刚刚起步——而不是40岁,在一部音乐剧的复兴中获奖。当我意识到什么也不会发生时,我想我还是继续工作吧。”
“我想把这部剧搬到百老汇
成千上万的人参观它,然后参观伦敦西区,然后参观澳大利亚和世界。我希望能够用它来服务他人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今天,正如他的新节目所象征的那样,克里尔正在享受更多地掌控自己的事业和选择。他想成为“在桌子的另一边”,导演、编剧和制片。他想监督弗兰克·洛瑟1956年的音乐剧《最快乐的家伙》的复兴。“我不需要去百老汇。我只是想做艺术。我有的是,”克里尔说。“总有一天我需要工作来支付账单,而外百老汇并不是摇钱树,但通过这部剧,我正在做我生命中最有创意的事情——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更多的机会。”
“这就是我想要的。我希望这部剧能在百老汇上演,让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它,然后巡演到伦敦西区,然后是澳大利亚和全世界。我希望能够用它来服务他人。如果我再也不拍电影或电视了,我可以接受,但我还没准备好再也不登台。我喜欢能够讲故事让人笑,让人哭,让人思考。”
“我很自豪,因为我承认自己是个荡妇,并为此感到自豪。我不能接受性耻辱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克里尔拒绝透露他现在是否有了新的伴侣——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,他短暂而快乐的微笑表明,也许答案是“有”——但是,他仍然带着愉快的微笑说,“我会说,我正处于一个愈合的地方,说实话,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到达。”在朋友和家人的支持、爱和敞开的心扉下,这意味着一切。”
克里尔说他一直在使用约会软件。“我从没想过我会这么做,但我有一点性觉醒。我很骄傲,因为我承认自己是个荡妇,并为此感到骄傲。我不能接受性耻辱。任何延续它的人都可以坐在我旁边,我会解释为什么你必须对那些想要探索性的人更友善,他们想要发现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是谁,只要他们是安全的,不伤害任何人。性是一种美丽的、探索的、充满活力的联系。我们都应该有自由去看它。”

沃尔特麦克布莱德摆
克里尔一直很害怕使用这款应用,直到他意识到他不是用它来认识任何人,而是为了消除他对约会应用的恐惧。“我在Hinge上玩得很开心,”他笑着说。“我可能不是最好的朋友。这是一种探索——约会,敞开心扉去认识真正了不起的人,他们都有自己不同的性或浪漫之旅。我正在学着多交流。”
离50岁还有三年,衰老显然是克里尔的心头大患。他笑着说,他被年轻的男人所吸引,而且“必须爱他身体和脸上发生的一切”(再一次,谦卑似乎是真诚的,但事实是,他客观上非常漂亮!)克里尔说,在过去,他给合伙人施加了太大的压力,让他们认可他,“我必须认可我自己。”我必须照镜子,爱我所看到的。是的,我的皮肤是下垂的,只有服用人类生长激素或坚持过度锻炼才不会下垂,而我不想这样做。我要相信有人会想要我因为他们想要我的身材因为我想要我的身材。

珍妮特·佩莱格里尼/盖蒂图片社
“当我在疫情中满45岁时,我意识到没有人会在乎一个45岁的人不喜欢自己的脸或身体。我拍了拍自己的手腕。我必须照镜子,不再看到25岁的矮胖,而是看到45岁的火辣。如果你能看到一个45岁的帅哥,那么你猜还有谁会看到一个45岁的帅哥?那些年轻人想和45岁的辣妹上床!唯一居高临下的声音就是我自己。人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我有多帅。我什么时候才能相信?外表美是很棒,但问题是:你还有什么?”
正如《走过》所暗示的那样,克里尔发现艺术,以及沉浸在大都会博物馆的经历,是一种治愈和启发。“博物馆给了我自由,”克里尔说。音乐也有类似的效果,尤其是现在“毫不掩饰的快乐和惊人的天赋”雅各布·科利尔。
“我接受我将在脑海中听到那个法官的声音,所以我会说,‘没关系’,然后站起来,再做一次。——加文·克里尔
事实上,音乐是克里尔正在创作的一部新戏剧作品的核心。在一个暂定名为《Loud Night》的节目中,一名男子在每个月圆的时候都会举办一场派对,伴随着电子音乐和电子舞曲,从午夜一直持续到太阳升起。它的唯一目的是让那些感觉被忽视的人感到被倾听、被关注和自由。
这种描述听起来就像我们谈话中的克里尔,也是我们在这部剧中看到的克里尔——最终放手,放手。他说,在情感上,一夜又一夜地挖掘出所有自传式的勇气和痛苦并不难。在每场演出中,他都试图“那天尽可能地敞开心扉,让情绪自然流露,不强迫任何其他情绪。”(选角导演)伯尼·特尔西(Bernie Telsey)最近告诉他,这部剧已经准备好了,克里尔可以把“编剧”留在家里,让“表演者”上场了。

蒂姆·惠特比/盖蒂图片社
这就是克里尔所做的。他说在每场演出结束时需要给自己一分钟。“我看着我的队友,担心一分钟,如果我浪费了他们的时间。我问自己,‘这对他们来说值得吗?他们觉得无聊吗?他们会厌倦讲这个故事吗?“这就是我今天的处境。我接受我将在脑海中听到那个法官的声音,所以我会说,‘没关系’,然后站起来,再做一次。”
克里尔泪流满面,突然湿润的眼睛里露出了微笑。“这让我想到就很激动。就像,我就在这里。”
相关文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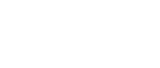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